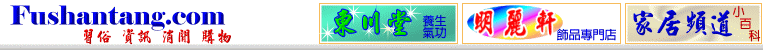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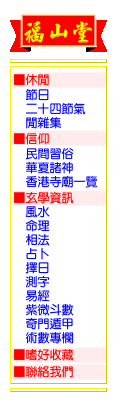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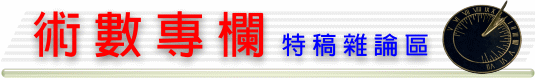
四柱预测学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概况 作者:不详
自古以来的历代学者们,都想站在本时代的理论高度对“天”做出尽量合理的解释,从而找出某一社会文化现象所产生的理论依据。
我们知道,算命做为华夏民族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由来已久,任何带有普遍现象的社会文化的产生都不可能因偶然因素突然发生,都有着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规律可循。因此,不了解命理文化现象的起源,就无法窥破它的性质,也难以把握命理文化活生生的精神命脉和内在机制,就不能正确地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一文化现象所造成的或正或负的社会功能。
即然把算命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那么,我们就得从这一现象的源头说起。
第一节、夏商周时代的天命观
所谓“天命”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定内容。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俱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而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只限于感性阶段,即混沌迷茫又神秘恐怖。出于生存之需要,这个时代人类在思维生发过程中没有闲心也不可能出现自觉的对个人命运规律的深邃的思考。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形容个人命运规律的命理文化。人类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消极地无可奈何地交给神秘恐怖的大自然,由此,又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崇拜心理。
中化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地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到高无尚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今二月,帝令不雨”。《铁云藏龟》
“今三月,帝令多雨”。《殷墟书契.前编》
“翼癸卯,帝其令风;翼癸卯,帝不令其风”《殷墟文字.乙编》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足其年”《殷墟书契.前编》
不光是自然界刮风下雨是天帝的意志,同时“天帝”也主宰一切社会人事。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
“厥初生民,时维姜……履帝武敏歆……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诗经.大雅.生民》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尚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尚的“天帝”,就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到级制。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既然“天命”是不可改变的,一切都得听从“天”的意志,那么人们何须算命,又有什么理由来形容命理呢?所以在夏、商及西周初年这一上帝命定论的天命观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命理文化根本没有扎根的土壤,也不存在算命的社会文化现象。
那个时代,人们在自我意识的领域中是一个黑暗蒙昧而可悲的时代。尽管我们的先民们用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像司母戊方鼎这样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但是森严残酷的奴隶制度剥夺了人对自我价值和个人命运思考的权力,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人们在严格的以血缘关系而定的社会地位的社会框架中,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永不改变的角色。或许偶尔他们也思考自己的命运,然而每当这时,他们只能把木然无神的目光转向冥冥的苍穹。
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
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候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尚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駡“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不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人的思维认识,总要受到已有知识的限制。那么提供给刚刚从黑暗的天命观的缝隙中探出头来研究个人命运这个新课题的思想资料又是什么呢?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最早提出人类生活所必须的五种基本物质的是殷周之际的箕子。《尚书.洪范》中记载了箕子关于五行之数的话后又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箕子不仅确定了基始物资,而且还根据它们的自然属性确定了别名,并且从味道上做了区分,这是比较高明的。
箕子的五行学说仍没有完全跳出生活之需的圈子,倒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在箕子的基点上往上蹦了蹦,摘到一科学的果实。他是我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倡导者,关于五行,他说:“先五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万物。”伯阳父把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当做世界的本源,是其它一切物资的基始。正是由于这五种不同的物质互相结合才生成了万物,显然,伯阳父企图用物质自身来说明客观世界。
五行说被高度抽象出来后,基本质不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是物质的五种基本形态。金木水火土只是这五种基本形态的代号。拿今天的话来说,金是固体态,水是液体态,火是气体态,木是等离子态,土是综合态,土包容一切,可被称为“第五态”物质。世界是动态的世界,而物质的运动必然引起此一物质和彼一物质之间的形态的转换,古人是用五行的生克制化来说明这一道理的。自然界阴阳相互作用产生了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则产生了万事万物无穷无尽的变化。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阴阳五行说的兴起和天地自然、生命形态、社会人事同源同理,同步效应的宇宙观的初建,不少学者以自然命定论来改换孔子的天帝命定论,并明确指出人的生死、寿夭、贵贱、贫富等都是“天之所禀”的自然之数。这是我国古代命运观上的重要转变,它的积极作用是对当时以宗法血缘定贵贱的封建制的巨大冲击,消极方面则是进一步否定了后天个人努力的作用和意义。如《淮南子 .谬称训》说:“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君子顺其在已者而已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人为的主观努力,在他们看来仅为一厢情愿的事,成功与否全在命在天,为了确立这一论点,《列子.力命》篇还煞费苦心的将“力”和“命”虚拟为两个人。
这段文章的大意是说,“力说,人的贫富贵贱,穷通寿夭,都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呀!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事。命说,即然如此,那么彭祖的才能比不上尧舜,而他却能活到八百岁;颜渊的才能高于众人,而只活了三十二岁;孔子的品德无疑高于诸候,却穷困一生;殷纣王极无品德,却高居帝王之位;季札是吴国的贤士,却一直无官;而蛮横的田桓却占有整个齐国;伯夷叔齐都贤,最后却饿死在首阳山上;鲁国的季氏虽恶但巨富,你要是有能力来改变这一切,为什么不去改变它呢?”《列子.力命篇》彻底否定人的后天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消极地“听天由命”的命运观,这是与高度极权统治的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经典的正统文化对“听天由命”的消极命运观的阐发远不止以上所述,但这些材料基本上道出了我国古代消极落后的旧命运观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两汉之际,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及王充的禀气说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但他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王充的自然命定论的理论是针对董仲舒的“天命论”和神学观而发的。他的“气一元”说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天命观”当然是个有力的抨击。
从殷周之际让我们的先民们望而生畏的“天帝命定论”到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的确立,又从两汉之际的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到王充的“自然命定论”,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然而任何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样式的理论的形成,都不能归之于某一个人的作用,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文化背景。
王充“禀气说”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不懂人的生理现象和动物的生理现象有着根本的不同,简单地以自然现象类推社会人事现象,“禀气说”的至命弱点是忽略了人后天的主观能动性及勤奋努力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陷入了神秘的“自然命定论”的泥坑。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和王充同时代的王符继承了王充“禀气说”的自然观,指出“千里之马,骨法虽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于器;士而弗仁,不成于位”《相列》。这就是说先天所禀赋的命禄没有后天的努力也不能实现。王符的“策马论”从根本上说,人的命运是“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贫富者也”他的这一见解,虽然谈不上在王充的“禀气说”基础上的一个飞跃,但起码是对王充自然命定论的一个重要修正和补充。
王充的“禀气说”为命理学的发展与其说是奠定了理论基础,不如说是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当时《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宇宙模式和董仲舒“天人相副”的出现,对今后命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节、唐宋时代,西洋占星术的引进,把命理文化推向理论的巅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聪明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唐以前历代的兴衰咎由,进而总结出“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经济上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诗《忆昔》)这样一个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汉代那种礼教的枷锁散架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特别是佛教的兴起,随着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入中土,大大促进了中土算命术的发展。
从宋元时代的文献记载得知,按着星象历法推算人命始于唐代贞元年间。在公元一八五年到八五○年这一时期,有西域康居国来的一个名叫李弼干的术士传来了印度婆罗门术《韦斯经》。有了原来的气候土壤,再加上外来术数的促进并融合,中国原有算命术的发展就振翅高飞了。
八字推命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它源远流长,由来已久,更为主要的是它是历朝历代命学大师的心血结晶,是东西文化交融而孕育出来的术数骄子。
相传它创始于战国时的鬼谷子、珞碌子,但依笔者之见,这恐怕是后人为了以神其说而做的“托辞”,多不可信。然而据说汉代的董仲舒、司马季主、东方朔、严君平和三国时的管辂、晋代的郭璞、北齐的魏定、唐朝以及五代的袁天纲、李淳风、僧一行、李泌、李虚中都有精于此术。甚至还传说李泌出游时得到了管略的命书《天阳诀》,又搜得盛唐时的高僧、历数天文家僧一行的命书《铜钹要旨》来占卜吉凶,百无一失。后来他将此术传给了李虚中。《玉照定真经》相传是晋代郭璞所作,是以年柱为己身的纳音推命术,而《珞碌子》也是仅以年柱为准的推命术,所有这些,都经过李虚中的创新发展为以年月日三柱为准的五行推命术,我国的四柱预测学由此产生了质的飞跃。后来此术又由五代时的麻衣道士陈希夷和徐子平继承,在徐子平手里,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又把它发展为以年月日时为准则,以日干为己身,以五行生克为演绎体系的六神(即十神)推命术。至此,四柱预测学才完成了它最关键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蜕变及质的飞跃。才以一个真正完整的面貌自立于华夏本土文化的术数之林。
第五节 明清之际对四柱预测学的系统整理及完善
唐宋以来在上层社会中的那种把论命做为雅谈的风气至明朝有增无减。诚如明人宋濂在 《禄命辩》中所说的“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者”。以至于达到了“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有大谈他人命者……”的程度,各种命理学著作也大量付梓、充斥书肆,这使得时人有了“自学成才”的入门途径,所以交流研讨命理,往往成为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的又一文雅的消遣。另外,自唐宋以来到明朝命理学热潮由上层社会下移到民间的势头更猛,使得举朝皆迷命理的浓厚民风。染化得平民百姓皆谙命学并成了一代风尚。据载,权贵孟无忌单马出巡,在江汉边遇到一个渔夫,提着一条大鱼让路于左,孟无忌问他年庚,不料生辰八字完全与自己相同,遂十分惊异,想邀请渔夫一同回去给他一个官做。渔夫谢绝道,我虽然和您年庚相同,但您生在陆地,所以命贵,我生在船中,水上漂浮,所以命贱,我每天以渔为生计也自足了,若一旦宝贵,命薄之人反而会不胜福份而暴死,说罢辞谢而去。一个朝廷重臣,一个江野渔人,但对命理精蕴的理解不分仲伯。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使得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算命习俗别俱特色。
由于明清以来我国命学热潮波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而命学各流派,门户也繁杂泛滥,这就势必形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有的术士对命学精典体会不深,持论有悖命理精蕴;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功夫,而用哗众取宠。没有来头的花拳绣腿炫人耳目,混迹江湖;有的机械套用命诀格局,将变化无穷的命理编排成死格式而对号入座(当今的计算机算命及软件算命),以致无法自圆其说;有的以上诸种情况兼而有之,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谈。更有甚者,有的人把预测机理稍加改头换面便自称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从古人的故纸堆扒拉出来的东西也纷纷付梓,实时国内易坛上真是即纷呈异彩又乌烟瘴气。所以在这轰轰烈烈的看命热潮中又潜伏着一种“学术不精则信者必寡”的信仰危机,命学要想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取得自身的发展,对命理文化就必须进行一番“去精取精,去伪存真”的系统的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从明朝初年即已开始。
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令解缙等人编辑的《永乐大典》把这之前的论命书无论质量如何多被编入,如果说被编入《永乐大典》的命书仅仅是随大流做出了一番登记造册的盘点的话,那么在这以后的许多命学家企图集大成的一些著作、则可视做为重建完整严谨的命学体系的自觉努力。在这类命学家中,万民英的建树最令人瞩目。他的命理学巨著《三命通会》被后世推崇为“采撮群言,得其精神”的经典著作,是对中国明代以前命理学的一次最为系统的彻底整理,以及对中国古代命理学的最高成就。
明代是四柱预测学理论发展和完善的鼎盛时期,当时除了万民英重建了命理学体系这一巨大工程外,比较有名而且质量较高的还有托名刘基写的《滴天髓》,沈孝瞻的《子平真诠》,张神峰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等。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由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由纪晓岚领衔篡修的《四库全书》,基本上包罗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命学的所有重要著作,以至于陈素庵的《命理约言》,任铁樵增注的《滴天髓阐微》,袁树珊的《命理探源》等一些命学著述,多半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夫造命书,先贤已穷尽天地精微之蕴而极矣。自唐李虚中一行禅师……其理雷同,至矣尽。无非金木水火土之微妙耳。今后学加增旨意口诀,莫非先贤已发之余意,大同小异……。”《渊海子平 .附子平真诠》这是说,自唐宋以来问世许多命学书籍,大多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基本上是对前人余意的引幽阐微,整理归纳。各书多有雷同之处或大同小异。
资料来源:摘录自互连网,谨供参考。
![]()
